我们为什么需要大数据交易所?
-
2023-03-28
来源:数据工匠俱乐部
“数据的价值在于反复利用(re-use)。”
长久以来,如何最大化数字经济核心生活要素——数据的价值,是各方念兹在兹的问题。
最近,随着《北京市促进数字经济创新发展行动纲要(2020-2022年)》《北京市关于打造数字贸易试验区的实施方案》《北京国际大数据交易所设立工作实施方案》的发布,通过数据交易所的数据交易成为对上述问题的最新回应。
据报道,“北京国际大数据”交易所肩负着“权威的数据信息登记平台、受到市场广泛认可的数据交易平台、覆盖全链条的数据运营管理服务平台、以数据为核心的金融创新服务平台、新技术驱动的数据金融科技平台”等五大功能,其未来引人无限遐想。
不过,在展望未来之时,不妨回顾一下过往的经验。
事实上,北京对大数据交易所并不陌生。早在2014年,全国首个大数据交易平台——中关村数海大数据交易平台就在中关村成立,而在全国范围内,贵阳大数据交易所、上海数据交易中心、重庆大数据交易平台、北部湾大数据交易中心等数十个交易平台亦在运营之中。
在此背景下,我们不禁要问:北京是否需要再设立一个新的大数据交易所?它是否会重蹈之前的覆辙?

▌大数据交易的痼疾
要回答“为什么需要大数据交易所”这个问题,还要从大数据交易的困境说起。
2018年4月,欧盟委员会在其《欧洲内公司间数据共享研究》(Study on data sharing between companies in Europe)中指出:数据提供方和数据需求方之间建立信任关系是实现数据交易的重要成功因素。
实际上,早在196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肯尼斯·阿罗就在《不确定性与医疗保健经济学》一文中分析了信任对数据市场的重要意义:信息(数据)与一般商品迥然有异,它有着难以捉摸的性质,买方在购买前因为不了解该信息(数据)无法确定信息的价值,而买方一旦获知该信息(数据),就可以复制,从而不会购买,故而信息(数据)是无法完全市场化的,这就是信息经济学的“阿罗悖论”。
在数据交易中,数据需求方因为难以判断数据的质量和价值,可能花了大价钱,却没有获得能实现预期目标的数据;数据提供方也因为缺乏有关需求方的信息,而低报了数据的价格,更不用说其对数据安全和数据滥用的担忧。
不仅如此,数据是典型的时效品,老数据不如新数据值钱,而且随着时间推移,前者越来越没有价值。就此而言,大数据与其说是“大”的数据,不如说是实时在线的“活”的数据,只有可信的数据提供方不断运行,才能避免数据的静态化和僵尸化,才能实现数据价值。
因此,与之前“数据库”(database)一次性买卖不同,大数据交易以“数据流”(data flow)的形式开展,而这更加依赖于双方的长期合作。如何克服信息悖论导致的“双边信任困境”,成为数据交易的根本问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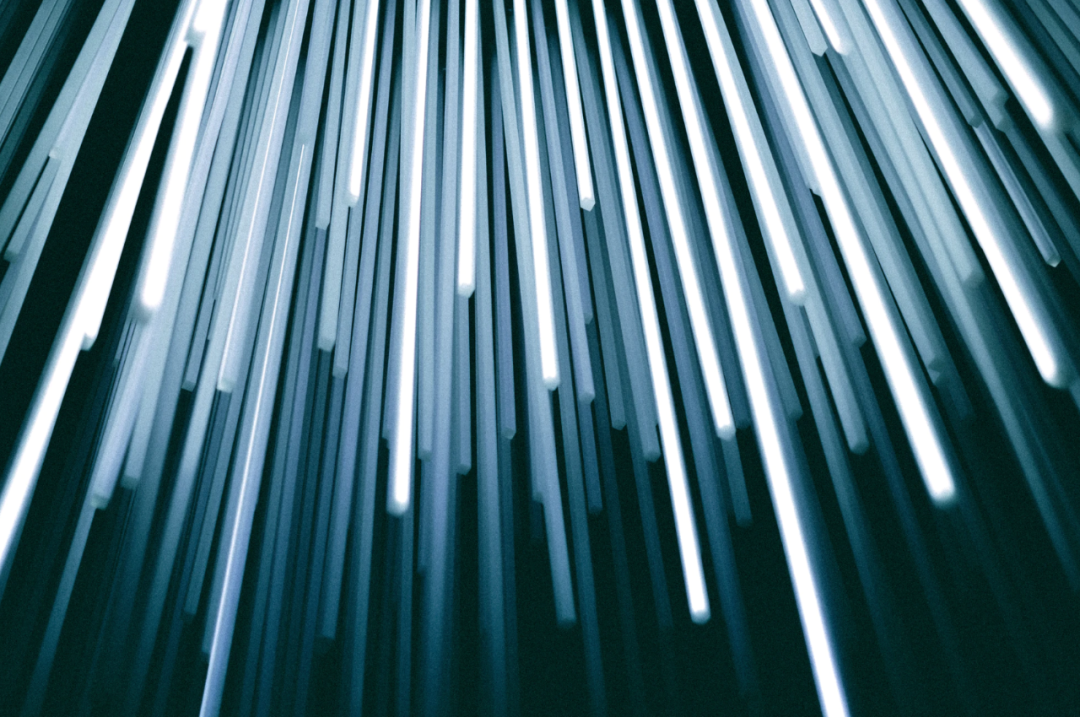
▌大数据交易的信任策略
面对大数据交易的双边信任困境,实践逐渐发展出如下三种信任策略:关系契约、数据担保和数据经纪人。
“关系契约”(Relational Contract)源于美国法学家麦克尼尔对现代社会的深入观察。他发现,一次为限的个别性契约在当代远不是普遍现象,相反,长期的、嵌入各种关系的契约才是常见的。
在大数据交易中,尽管其一般以正式书面合同为基础,但是,由于数据提供方之前数据的合法性和价值,以及数据需求方的后续行为均难以监控和验证,而数据安全事件更是无法预料的,双方不得不将很多条款悬而不决,留待以后根据情况变化再做随机应变的调整。
契约的“不完全性”使得双方试图寻求一种连续性的和关系性的合同过程,而不再是一次简单的利益交换,长期关系的期待以及内化于契约之中的合作、责任、风险、权利等社会因素,提供了“完全履行”合同的激励。
正因如此,建立稳定的朋友关系和人际信任成为重要的信任策略。不惟如是,为了打造利益共同体,数据提供方和需求方还通过股权、资产、业务关系,实现正式的或半正式的控制,以遏制当事人的投机行为。

同时,这一关系所具有的动态性和不断完善的特性,也赋予了数据交易以公正性。实践中,主要的数据交易一般发生在关联企业和合作伙伴之内,恰恰就是关系契约的明证。
当交易双方没有长期关系可依赖时,基于数据的“担保”就成为可行路径,这体现为数据的彼此共享,其实质是数据相互“许可”(silence)。
在这一场景下,双方相互让渡自己的数据使用权,每个共享人既是数据提供方,也是其他主体提供的数据的需求方。权利义务的交互性使得相互交换的数据和共享的数据池成为各方履约的隐含“担保”,从而为双方信任搭建挑梁。
最后,当双方确实无法信任时,独立的专业第三方——数据经纪人(data broker)成为重要的替代方案。作为美国数据市场中最重要的市场力量,数据经纪人从各种各样的来源购买、收集、汇总、处理包括消费者信息在内的各种数据,然后将数据出售于客户,用于验证个人身份、区分记录、营销产品以及防止金融欺诈等目的。
数据经纪人身为长期从事数据交易的第三方,重复博弈、声誉机制和违约成本,使得数据经纪人值得信赖。同时,数据经纪人也发挥着“守门人”的功能。在遴选和甄别客户的过程中,数据经纪人采取发放认证问卷、现场核实业务地址、进行互联网调查以及与潜在客户会面或交谈等方式,以判断潜在客户数据和业务的合法性。
关系契约、数据担保和数据经纪人虽然在一定程度上纾解了“双边信任困境”,但总体而言,或者适用范围狭窄(“数据担保”),或者适用条件苛刻(“关系契约”),或者有赖于市场培育与演进(“数据经纪人”),均无法满足我国发展数据要素市场的需求。在此背景下,大数据交易所应运而生。

▌大数据交易所的再出发
“大数据交易所”并非法律概念,这里,我们不妨将其界定为“为数据交易双方或者多方提供网络经营场所、交易撮合、信息发布等服务,供交易双方或者多方独立开展交易活动的自律性管理的法人。”
作为第三方中介平台,大数据交易所推动之前一对一的双边数据市场,向“一对多”或“多对多”的网络数据市场转型,数据市场的规模和效率由此倍增。然而,理论是一回事,现实是另一回事。
对我国各大数据交易所的调研发现,五年过去,很多大数据交易所成交寥寥,依然处于小规模的探索阶段。这种乏善可陈的局面固然源于数据权属和风险分担不明的法律痼疾,但直接原因却是大数据交易所定位与功能之困。正如浙江大数据交易中心副总来磊先生所言:“大家只是通过交易中心来接触一些客户,交易过程本身并不依赖交易中心来开展,我们更像是数据撮合类业务的服务商。”
面对前车之鉴,北京大数据交易中心如欲真正成为“数据交易中心”,必须改弦易撤,摆脱单一的场所提供者的束缚,积极介入交易流程,从破除“双边信任困境”出发,重新定位自身角色。
大数据交易中心首先是“认证者”。这意味着大数据交易中心应当确立交易方准入资质,审查申请人的组织形式、经营业绩、业务人员、技术风险防范等条件,向相关各方甄别和推荐有良好声誉的数据提供方和数据需求方,降低数据交易中搜寻和调查交易方的成本,从而创造价值。

其次,大数据交易中心是“撮合者”。作为多边市场的运营方,数据交易中心应培育一个囊括数据提供者、数据需求者、数据处理者、数据经纪人、数据服务者等各种主体的完整生态圈,凭借不同参与方的互补性和网络效应,利用差异化的定价策略来优化市场结构,推动供需之间的高效匹配,以降低交易中的“磋商成本”。
此外,大数据交易中心还是“监督者”。人的本性就是如果有人监视就会表现得不同:更和善、更努力、更诚信。麻省理工学院曾经进行过一个精妙的实验,研究者使用了一个名叫“天命”的社交机器人——由金属配件和一对能够追踪并捕捉运动的电子眼构成——监视参与者向诚实箱投钱的行为。
当“天命”在监视时,钱箱里的钱多了29%。为了防范数据交易中的机会主义行为(特别是数据滥用),大数据交易中心不但可以提供数据管理系统、安全计算系统、数据加密算法等技术服务,确保数据安全与可追溯,还可以通过强制性的信息披露和第三方审计以及违规处罚措施,确保各方全力以赴、互相合作和保持诚信。
最后,大数据交易中心还是“冲突化解者”。面对利益既一致又冲突的参与方,大数据交易中心一方面要提供合同模本和交易规则,确立激励相容的治理架构,另一方面,大数据交易中心应建立“在线争议解决机制“(ODR),把各方争议分解成可量化的要素,通过证据智能提交、质证、类案处理的程序,作出快捷、经济、公平的裁决,大幅降低交易方的救济成本。
同时,为了提升透明性和包容性,大数据交易中心还可以引入专家评审和会员评审,当事人可以在相应的评审员库中各自选择评审员,组成评审团作出裁决。
如肯尼斯・阿罗所言:“几乎所有商业交易都包含信任元素,有时间跨度的交易更是如此。可以合理推论,世上大部分经济落后可用缺乏互信来解释。”
我国大数据交易的滞后亦是如此。恰恰因为当事人缺乏信任,作为第三方的大数据交易中心才凸显价值。因而,北京大数据交易中心能否成功,端看其成为大数据交易网络中的核心节点与关键平台,以及是否满足交易各方重建信任的期待。
就此而言,北京大数据交易中心的成立固然可以依赖政府之手,但成功必须根植于其对数据要素市场的洞察和贡献之中。
- 推荐
- IT/互联网
- CIO
- CDO
- 运营
- IT
- 供应链/生态
- 大数据
下一篇
推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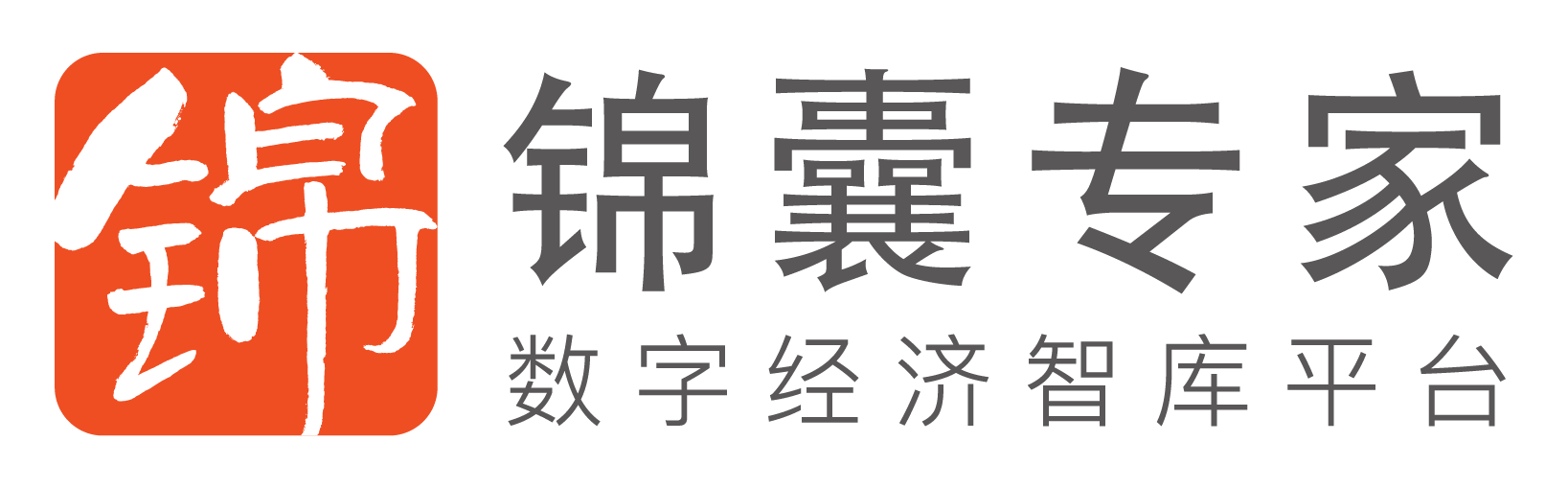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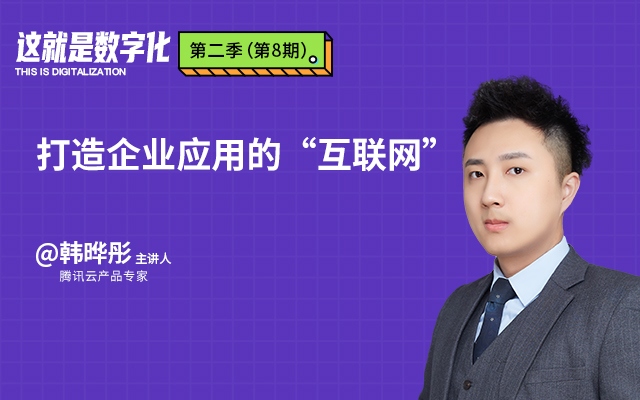




我要评论